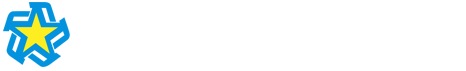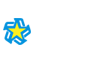濟(jì)南商務(wù)調(diào)查公司了解到從1997年刑法頒布至今已有20年,制裁網(wǎng)絡(luò)犯罪的刑事立法與司法解釋不斷推陳出新。截至目前,先后出臺(tái)了16部法律文件,涉及數(shù)十種犯罪類型。對(duì)這20年間涉及網(wǎng)絡(luò)犯罪的法律文件的貢獻(xiàn)進(jìn)行理論化的歸納與提升,系統(tǒng)總結(jié)主要成就和有益經(jīng)驗(yàn),在此基礎(chǔ)上探索網(wǎng)絡(luò)刑法的未來(lái)發(fā)展方向與中國(guó)刑法應(yīng)有的理論貢獻(xiàn),頗有現(xiàn)實(shí)意義。
網(wǎng)絡(luò)時(shí)代下立法與司法的關(guān)系:司法探索與立法最終確立
按照刑法學(xué)原理,由于刑法本身就是一種“暴力”,因此,需要受到理性的束縛與約束,此種束縛與約束在技術(shù)上表現(xiàn)為罪刑法定原則。在農(nóng)業(yè)社會(huì)和工業(yè)社會(huì),由于科學(xué)技術(shù)與社會(huì)發(fā)展進(jìn)程的相對(duì)穩(wěn)定和緩慢,罪刑法定原則約束下的刑法能夠較為順利地應(yīng)對(duì)實(shí)踐中出現(xiàn)的絕大部分問(wèn)題。
伴隨著社會(huì)發(fā)展速度大幅加快,各種新技術(shù)、新事物層出不窮,受罪刑法定原則“束縛”的刑法在面對(duì)實(shí)踐中的新問(wèn)題時(shí)越來(lái)越顯得捉襟見(jiàn)肘。因此,有節(jié)制地?cái)U(kuò)張解釋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而這種“擴(kuò)張”本身,既是為現(xiàn)實(shí)所迫的被動(dòng)舉措,也是為下一步立法進(jìn)行探索的主動(dòng)選擇。借助司法文件相對(duì)“短平快”的特點(diǎn),司法為立法“鋪路”和互相配合,司法層面以司法解釋等手段先行探索,待理論成熟、時(shí)機(jī)具備之后再通過(guò)立法的形式予以最終確認(rèn),成為制裁網(wǎng)絡(luò)犯罪的一種思路。
刑事司法探索的理論梳理
刑事司法的貢獻(xiàn),在于在立法沒(méi)有明確規(guī)定的情況下,率先摸索出一套回應(yīng)司法實(shí)踐困惑和需求的處理規(guī)則。過(guò)去的探索,主要包括以下幾個(gè)方面:
新生事物性質(zhì)之明確
網(wǎng)絡(luò)的飛速發(fā)展,各種新生事物層出不窮,對(duì)于這些新事物的內(nèi)涵以及其在法律上的地位往往一開(kāi)始并不明確,這就需要通過(guò)解釋予以規(guī)定。對(duì)于網(wǎng)絡(luò)犯罪涉及的新生事物的刑法性質(zhì)明確,司法解釋進(jìn)行了積極探索:(1)網(wǎng)頁(yè)鏈接:由于直接在網(wǎng)絡(luò)上發(fā)布違法犯罪信息的方法過(guò)于直接,現(xiàn)實(shí)中犯罪分子多采取更隱蔽的做法,即將指向各種違法犯罪信息的網(wǎng)頁(yè)鏈接發(fā)布在網(wǎng)絡(luò)上。對(duì)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guān)于辦理利用互聯(lián)網(wǎng)、移動(dòng)通訊終端、聲訊臺(tái)制作、復(fù)制、出版、販賣、傳播淫穢電子信息刑事案件具體應(yīng)用法律若干問(wèn)題的解釋(一)》(下稱《解釋(一)》)對(duì)網(wǎng)頁(yè)鏈接的性質(zhì)和內(nèi)容進(jìn)行了明確,將網(wǎng)絡(luò)鏈接本身行為解釋為等同于發(fā)布鏈接背后的信息。(2)通訊群組:通訊群組這種帶有“半封閉性”的交流平臺(tái)帶來(lái)交流便利的同時(shí),也讓各類違法犯罪信息可以在通訊群組中相對(duì)公開(kāi)地傳播,催生出了各類違法犯罪活動(dòng)。對(duì)此,《關(guān)于辦理利用互聯(lián)網(wǎng)、移動(dòng)通訊終端、聲訊臺(tái)制作、復(fù)制、出版、販賣、傳播淫穢電子信息刑事案件具體應(yīng)用法律若干問(wèn)題的解釋(二)》(下稱《解釋(二)》)對(duì)網(wǎng)絡(luò)通訊群組傳播性質(zhì)進(jìn)行了認(rèn)定,對(duì)于通訊群組的建設(shè)者和管理者,在性質(zhì)上等同于傳播者。對(duì)此,2017年國(guó)家互聯(lián)網(wǎng)信息辦公室發(fā)布的《互聯(lián)網(wǎng)群組信息服務(wù)管理規(guī)定》也再次明確了通訊群組的建立者、管理者應(yīng)當(dāng)履行群組管理職責(zé)。(3)網(wǎng)絡(luò)空間:隨著網(wǎng)絡(luò)自身的不斷發(fā)展,對(duì)網(wǎng)絡(luò)空間秩序的破壞與對(duì)現(xiàn)實(shí)空間秩序的破壞是一樣的,都會(huì)造成社會(huì)秩序的紊亂。因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guān)于辦理利用信息網(wǎng)絡(luò)實(shí)施誹謗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wèn)題的解釋》(下稱《網(wǎng)絡(luò)誹謗解釋》)規(guī)定,對(duì)于利用信息網(wǎng)絡(luò)辱罵、恐嚇?biāo)耍楣?jié)惡劣,破壞社會(huì)秩序的,依照尋釁滋事罪定罪處罰,從而明確了網(wǎng)絡(luò)空間、網(wǎng)絡(luò)秩序的公共場(chǎng)所、公共秩序?qū)傩浴?
關(guān)鍵詞的“技術(shù)性更新”與“規(guī)范化轉(zhuǎn)型”
針對(duì)計(jì)算機(jī)信息系統(tǒng)的犯罪,現(xiàn)有的計(jì)算機(jī)犯罪罪名體系已經(jīng)足夠。因此,增設(shè)新罪名無(wú)大必要,挖掘現(xiàn)有罪名的潛力、通過(guò)對(duì)現(xiàn)有罪名進(jìn)行時(shí)代性的解釋,足以回應(yīng)現(xiàn)實(shí)發(fā)展:(1)關(guān)鍵詞的“技術(shù)性更新”。隨著技術(shù)的不斷革新,對(duì)于現(xiàn)有罪狀中的關(guān)鍵詞有予以更新的必要。2013年《關(guān)于依法懲處侵害公民個(gè)人信息犯罪活動(dòng)的通知》在刑法領(lǐng)域?qū)Α肮駛€(gè)人信息”的概念進(jìn)行了界定,但在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guān)于辦理侵犯公民個(gè)人信息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wèn)題的解釋》中對(duì)“公民個(gè)人信息”概念進(jìn)行了二次解釋,明確將“行蹤軌跡”和“活動(dòng)情況”納入進(jìn)來(lái),這兩類信息實(shí)際是在三網(wǎng)融合時(shí)代手機(jī)定位功能越發(fā)普遍也越發(fā)強(qiáng)大的背景下才凸顯出來(lái)的。(2)關(guān)鍵詞的“規(guī)范化轉(zhuǎn)型”。關(guān)鍵詞的技術(shù)性更新是一方面,關(guān)鍵詞的規(guī)范化更有必要。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guān)于辦理危害計(jì)算機(jī)信息系統(tǒng)安全刑事案件應(yīng)用法律若干問(wèn)題的解釋》(下稱《信息系統(tǒng)解釋》)對(duì)計(jì)算機(jī)信息系統(tǒng)的“控制權(quán)”進(jìn)行了規(guī)定,通過(guò)將出售“控制權(quán)”視為贓物犯罪處理的方式,將它解釋為“財(cái)物”。雖然此種解釋的科學(xué)性有待商榷,但這是對(duì)“贓物”這一規(guī)范性關(guān)鍵詞在信息時(shí)代的擴(kuò)張解釋。
定性規(guī)則之確立
對(duì)新生事物明確性質(zhì)僅僅只是問(wèn)題的一部分。對(duì)于構(gòu)成要件的認(rèn)定、行為性質(zhì)的判斷,則是一個(gè)更亟待解決的問(wèn)題。司法解釋對(duì)此也予以關(guān)注:(1)片面幫助犯:片面共犯理論對(duì)于其成立范圍一直存有爭(zhēng)議。但在網(wǎng)絡(luò)犯罪時(shí)代,片面共犯理論能夠很好地解決由于網(wǎng)絡(luò)的虛擬性以及“一幫多”的共同犯罪現(xiàn)象所帶來(lái)的共犯認(rèn)定難題。《解釋(一)》中,規(guī)定了網(wǎng)絡(luò)傳播淫穢信息犯罪中的片面共犯成立空間,通過(guò)司法解釋突破了共同犯罪的傳統(tǒng)通說(shuō)觀點(diǎn);《信息系統(tǒng)解釋》規(guī)定了危害計(jì)算機(jī)信息系統(tǒng)安全犯罪中可以普遍成立片面共犯;而《網(wǎng)絡(luò)誹謗解釋》則對(duì)利用網(wǎng)絡(luò)實(shí)施犯罪的片面共犯進(jìn)行了廣泛性承認(rèn)。(2)共犯行為正犯化:網(wǎng)絡(luò)時(shí)代,“共犯行為正犯化”理論的確認(rèn)是一個(gè)大的進(jìn)步,追求的是共犯行為處罰的獨(dú)立性。《解釋(二)》提出了網(wǎng)絡(luò)傳播淫穢信息犯罪中的“共犯的正犯化”解決思路,首次將共犯行為獨(dú)立為正犯化行為,突破了傳統(tǒng)理論的束縛,為實(shí)踐中認(rèn)定網(wǎng)絡(luò)犯罪的幫助行為指明了方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guān)于辦理網(wǎng)絡(luò)賭博犯罪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wèn)題的意見(jiàn)》則明確了網(wǎng)絡(luò)賭博犯罪中的共犯正犯化,進(jìn)一步擴(kuò)展了共犯正犯化的司法解釋思路。
定量標(biāo)準(zhǔn)之重構(gòu)
網(wǎng)絡(luò)時(shí)代對(duì)于定量因素適時(shí)地予以調(diào)整,對(duì)犯罪的定量體系進(jìn)行重構(gòu)以做到正確評(píng)價(jià)是必需的。司法解釋也進(jìn)行了相應(yīng)調(diào)整:(1)點(diǎn)擊數(shù):“點(diǎn)擊數(shù)”能夠直觀反映出違法信息的實(shí)際傳播量。因此,《解釋(一)》對(duì)網(wǎng)絡(luò)違法信息傳播犯罪的定量標(biāo)準(zhǔn)進(jìn)行了規(guī)定,將“實(shí)際被點(diǎn)擊數(shù)”作為認(rèn)定傳播淫穢電子信息的標(biāo)準(zhǔn)之一,這是司法上第一次針對(duì)網(wǎng)絡(luò)犯罪引入了新定量模式,自此“點(diǎn)擊數(shù)”成為新的刑法量化標(biāo)準(zhǔn)。(2)注冊(cè)會(huì)員:“注冊(cè)會(huì)員”反映出違法犯罪信息傳播的群體大小。《解釋(一)》對(duì)網(wǎng)絡(luò)違法信息傳播犯罪的定量標(biāo)準(zhǔn)進(jìn)行了規(guī)定,將“注冊(cè)會(huì)員”作為認(rèn)定傳播淫穢電子信息的標(biāo)準(zhǔn)之一。(3)瀏覽:“瀏覽量”與“點(diǎn)擊數(shù)”相似,都能夠反映出違法信息的實(shí)際傳播數(shù)量,只是前者是相對(duì)于網(wǎng)頁(yè)來(lái)說(shuō),后者則是相對(duì)于網(wǎng)站而言。《網(wǎng)絡(luò)誹謗解釋》增加“瀏覽”作為網(wǎng)絡(luò)違法信息傳播犯罪的定量新標(biāo)準(zhǔn)。(4)轉(zhuǎn)發(fā):“轉(zhuǎn)發(fā)”行為是把違法信息通過(guò)自己再次傳播,它實(shí)質(zhì)是一種幫助犯。《網(wǎng)絡(luò)誹謗解釋》增加“轉(zhuǎn)發(fā)”作為網(wǎng)絡(luò)違法信息傳播犯罪的定量新標(biāo)準(zhǔn)。
刑事立法的探索與時(shí)代貢獻(xiàn)
對(duì)于司法實(shí)踐中經(jīng)過(guò)積極探索和檢驗(yàn)行之有效地制裁網(wǎng)絡(luò)犯罪的具體規(guī)則,刑事立法予以認(rèn)可和提升轉(zhuǎn)化為法條的頗多。
制裁網(wǎng)絡(luò)犯罪法網(wǎng)編織的初步完成
這一工作,實(shí)際上包括兩個(gè)部分:(1)刑法第287條的“雙通道”擴(kuò)張解釋。就條文而言,規(guī)定的是“利用計(jì)算機(jī)實(shí)施犯罪”,實(shí)際上悄然擴(kuò)充到“利用網(wǎng)絡(luò)實(shí)施犯罪”。2000年全國(guó)人民代表大會(huì)常務(wù)委員會(huì)《關(guān)于維護(hù)互聯(lián)網(wǎng)安全的決定》明確規(guī)定,“利用互聯(lián)網(wǎng)實(shí)施……犯罪的,依照刑法有關(guān)規(guī)定追究刑事責(zé)任”,這一單行刑法的歷史意義和貢獻(xiàn)都難以估量:一方面,通過(guò)“解釋型單行刑法”打通了實(shí)施傳統(tǒng)犯罪和利用網(wǎng)絡(luò)實(shí)施傳統(tǒng)犯罪適用同一制裁條款的通道,讓刑法從傳統(tǒng)社會(huì)延伸進(jìn)入了“網(wǎng)絡(luò)社會(huì)”;另一方面,借機(jī)將“利用計(jì)算機(jī)”和“利用網(wǎng)絡(luò)”予以等同化,擴(kuò)張了刑法第287條的適用范圍。(2)罪名的體系化完善。真正開(kāi)始大規(guī)模地對(duì)網(wǎng)絡(luò)犯罪進(jìn)行立法,則始于刑法修正案(九)。在吸取了多年的實(shí)踐經(jīng)驗(yàn)、整合了多部司法解釋的經(jīng)驗(yàn)總結(jié)后,刑法修正案(九)構(gòu)建了信息時(shí)代下網(wǎng)絡(luò)犯罪罪名體系。
宏觀層面的三種責(zé)任模式之確立
刑事立法通過(guò)“共犯行為正犯化”“預(yù)備行為實(shí)行化”和“網(wǎng)絡(luò)服務(wù)提供者的平臺(tái)責(zé)任”三種責(zé)任模式,初步實(shí)現(xiàn)了制裁網(wǎng)絡(luò)犯罪的責(zé)任追究模型。(1)共犯行為正犯化。對(duì)于共犯行為正犯化理論,它的內(nèi)涵在于兩方面,一是“定性獨(dú)立化”,即認(rèn)定犯罪、追究責(zé)任時(shí)對(duì)于幫助犯可以脫離實(shí)行犯而單獨(dú)、直接定罪;二是“評(píng)價(jià)正犯化”,即由于網(wǎng)絡(luò)時(shí)代“一幫多”現(xiàn)象的大量存在,以及技術(shù)性幫助行為的地位躍升,使得傳統(tǒng)理論中被視為從犯、共犯的幫助犯,在評(píng)價(jià)上應(yīng)當(dāng)被視為主犯、正犯予以量刑處罰。刑法第287條之二規(guī)定了“幫助信息網(wǎng)絡(luò)犯罪活動(dòng)罪”,對(duì)于網(wǎng)絡(luò)犯罪的幫助犯予以獨(dú)立入罪。(2)預(yù)備行為實(shí)行化。預(yù)備行為實(shí)行化是將原本是其他犯罪的預(yù)備行為按照實(shí)行行為予以處罰。預(yù)備行為實(shí)行化具有兩個(gè)效果:一是對(duì)于預(yù)備行為處罰的獨(dú)立化,二是刑法打擊時(shí)點(diǎn)的前移,涉及網(wǎng)絡(luò)安全的犯罪,如果等到危害結(jié)果發(fā)生再去處罰,可能導(dǎo)致危害后果難以估量或者無(wú)法測(cè)量。刑法第287條之一規(guī)定了“非法利用信息網(wǎng)絡(luò)罪”,對(duì)于利用網(wǎng)絡(luò)設(shè)立違法犯罪的網(wǎng)站、通訊群組,以及發(fā)布違法犯罪信息的行為,予以定罪處罰。(3)網(wǎng)絡(luò)服務(wù)提供者的平臺(tái)責(zé)任。信息時(shí)代,網(wǎng)絡(luò)平臺(tái)的建立者、管理者有某種“二政府”的身份和責(zé)任,對(duì)于平臺(tái)上的違法犯罪行為不允許持視而不見(jiàn)甚至縱容的態(tài)度,因此,強(qiáng)調(diào)平臺(tái)的法律責(zé)任乃至刑事責(zé)任是一種必然的趨勢(shì)。刑法第286條之一規(guī)定了“拒不履行信息網(wǎng)絡(luò)安全管理義務(wù)罪”,由此給網(wǎng)絡(luò)服務(wù)提供者明確了新的刑法義務(wù)即網(wǎng)絡(luò)安全管理義務(w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