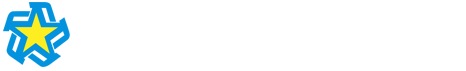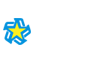在日常生活中,“私家偵探”(1)一直是披著神秘面紗的存在,大家對其既熟悉又陌生。作為一個舶來品,“私家偵探”在我國的發展歷程僅有短短三十年。一直以來“私家偵探”這一職業并未被我國官方所認可,其所開展的調查業務是否觸犯我國刑事法律存在一定爭議。本文試從刑事實務視角,對“私家偵探”調查行為的法律定性爭議進行厘清和分析。
一、“私家偵探”在我國的發展歷史及法律地位
(一)由機構到公司,“私家偵探”在夾縫中求生存
在我國,“私家偵探”的出現始于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私家偵探”性質機構,常以“安全事務調查所”、“民事事務調查所”、“社會經濟事務偵探所”等名義存在,業務范圍涵蓋民事、經濟糾紛受理、債務追索、親友查找、個人隱私調查等方面。由于這些經營業務缺乏相關法律依據,部分業務范圍與現有國家司法機關職能分工相沖突,開展業務的一些手段違反法律規定,產生了一系列社會問題。為此,公安部于1993年9月7日發布《關于禁止開設“私人偵探所”性質的民間機構的通知》(下文稱1993年《通知》),嚴禁任何單位和個人開辦私人偵探所性質的民間機構,并對現有私人偵探所性質的民間機構進行清理和取締(2)。
在國家的嚴厲打擊之下,“私家偵探”機構紛紛改頭換面,通過注冊公司的方式化身為各種各樣的“調查公司”或“咨詢公司”(下文簡稱“私家偵探”公司)繼續存在于我國各大中城市。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公眾在資金信用、夫妻忠誠度、知識產權、尋人尋址找物等方面的調查取證需求持續增長,而相關國家機關運用公權力進行調查取證的范圍又十分有限,“私家偵探”公司提供的調查取證業務正好能填補這一空白,因此,盡管處于法律灰色地帶,但“私家偵探”公司仍在我國得到了穩步發展。
(二)“私家偵探”公司開展的調查業務及其行為模式
在具體開展的業務方面,由于這些“私家偵探”公司在工商部門登記注冊時往往將經營范圍定位在法律咨詢、商務調查、市場調查、知識產權咨詢、企業財務咨詢服務、商業調查服務、婚姻信息咨詢、安全系統監控、網絡安全信息咨詢等方面,具有一定的隱蔽性。加之實際開展的業務中確實包含部分正當合法業務,導致實務中對這類公司的合法性認定帶來了一定困難。
盡管包裝形式多樣,但“私家偵探”公司實際開展的經營項目仍以婚外情調查、找人尋址、手機信息查詢、代人討債等傳統業務為主,其中更是以婚外情調查、找人尋址為代表的調查業務為核心。實踐中,這類調查業務的具體行為模式是:委托人(客戶)先與“私家偵探”公司簽訂相關委托調查協議,然后由委托人提供被調查人的手機號碼、車牌號碼、住址等基礎信息,再由“私家偵探”公司指派具體的調查員(外勤人員)通過采取車輛定位、跟蹤蹲守、偷拍照片、偷錄視頻、查詢被調查人開房記錄、通話記錄等方式進行調查,并將調查獲取的相關信息經整理打包后提供給委托人,完成調查任務。
“私家偵探”公司在調查權上的“先天不足”,決定了其在實施上述調查行為時不可避免地需要借助定位、跟蹤、偷拍偷錄等非法手段。而無論是其調查過程還是結果,也都必然會在不同程度上對公民個人隱私領域造成侵害。因此,在國家持續加大對公民個人信息保護力度的大背景下,對“私家偵探”公司調查行為性質的認定從行政層面上升至刑事層面,成為必然。
二、我國刑事司法實務中對“私家偵探”調查行為的定性
在刑事法律層面,對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的相關規定經歷了從無到有、再到不斷修改與完善的過程,相應的,刑事實務中對“私家偵探”調查行為的性質認定也由模糊不斷趨向明確。
(一)刑法修正案(七)施行之前,我國對此類調查行為缺乏具體法律法規進行規制,是否構成犯罪存在爭議
刑法修正案(七)施行之前,我國針對商務調查行為并沒有具體的法律法規進行規范,對公民個人隱私保護亦缺乏刑法層面的具體規定,因此,“私家偵探”開展的調查活動是否構成犯罪存在爭議。一種觀點主張“私家偵探”從事的調查活動構成犯罪。理由是“私家偵探”機構或公司以企業經營的形式對外從事調查活動,調查過程通常伴隨著跟蹤、偷拍等非法方式,不僅會對被調查人的個人隱私造成侵犯,而且還擾亂了市場經濟秩序和社會管理秩序,具有現實和潛在的社會危害性,應認定為構成非法經營罪;另一種觀點則認為,“私家偵探”機構或公司的調查行為源于委托人的委托,法律并不禁止委托人自行行使調查權利,當然也不應禁止委托人將該權利委托給這些機構或公司代為行使,故“私家偵探”的調查行為缺乏刑法意義上的可界定性,不應認定為犯罪。另外認為,“私家偵探”的調查行為并不符合非法經營罪的犯罪構成,也不應構成非法經營罪。
在司法實務中,雖然對此類調查行為基本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但應當看到,此階段更多的“私家偵探”案件實際并未進入刑法規制視野,而是依據1993年《通知》等規定,僅在行政層面予以清理和取締。
(二)刑法修正案(七)增設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規定,為打擊“私家偵探”的調查行為提供了法律依據
2009年2月28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七)在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條增設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的規定(3),為打擊“私家偵探”的調查行為提供了刑事法律依據。但由于當時關于“公民個人信息”的范圍并沒有相應的法律、司法解釋作出明確規定,實踐中對其含義和適用范圍存在不同認識,尤其對個人日常行蹤之類的活動記錄是否屬于“公民個人信息”存在較大爭議,導致實務中對“私家偵探”調查行為的性質認定仍存在分歧。有以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定罪量刑的。如,湖南省長沙市望城區人民法院審理的李某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案,被告人李某利用其在互聯網上注冊的“湖南三贏調查事務”網頁,向社會發布承接私家偵探、婚姻調查等業務的廣告信息,并通過騰訊QQ向他人購買公民身份信息、住宿信息、手機通話詳單等個人信息后,將其販賣給下家并從中牟利。該行為最終被法院認定構成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4);也有以非法經營罪定罪量刑的,如:2010年3月,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對李某等4名有償非法從事跟蹤、拍照、定位等活動的“私家偵探”,以非法經營罪判處(5)。又如,福建省泉州市鯉城區人民法院審理的陳某甲非法經營一案,法院認定被告人陳某甲為非法牟利,雇傭他人非法經營“私人偵探”業務,擾亂市場秩序,其行為已構成非法經營罪(6)。
最高院《刑事審判參考》第1007號指導案例認為,公民所處的具體位置、日常行動軌跡和活動地點等信息,涉及家庭住址、單位地址、經常出入的場所等公民隱私和生活習慣性內容,具有個人專屬性,能反映出該公民某些個人特征,且信息內容關系到公民日常生活的基本安全性,信息的泄露會使公民徹底失去安全感,嚴重影響其日常生活。因此,公民的行蹤屬于刑法所保護的“公民個人信息”(7)。該指導案例首次明確了通過非法跟蹤他人行蹤所獲取的公民日常活動信息屬于公民個人信息,為“私家偵探”案件的認定統一了司法裁判尺度。
(三)刑法修正案(九)(8)進一步修改和完善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規定,“私家偵探”調查行為的定性趨向明確
刑法修正案(九)對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一進行了修改,不僅增加規定了一般主體違規向他人出售、非法提供公民個人信息的犯罪,而且擴大了原來第一款規定的犯罪主體范圍,并將“違反國家規定”修改為“違反國家有關規定”,同時規定了從重處罰的情節(9)。在罪名上,也由原來的出售、非法提供公民個人信息罪及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多個罪名,統一為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一個罪名。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7]10號)對“公民個人信息”的含義和范圍作出了明確規定:“公民個人信息是指以電子或者其他方式記錄的能夠單獨或者與其他信息結合識別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動情況的各種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證件號碼、通信通訊聯系方式、住址、賬號密碼、財產狀況、行蹤軌跡等。”該規定明確公民個人信息的范圍不僅包含識別信息,而且包含活動信息。
隨著上述法律規定的修改和完善,“私家偵探”調查活動的性質趨向明確。對“私家偵探”調查活動以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進行認定,基本在司法實務中達成了共識。如:浙江省義烏市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汪海濤、李加俊對外承接“私人偵探”業務,利用非法手段為他人提供軌跡信息、住宿信息、財產信息、銀行信息、車輛信息、人口信息等公民個人信息并進行牟利,其行為構成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10);被告人周禮鋒因在互聯網上以“順德一牛私家偵探”為名招攬生意、非法經營私家偵探業務,同樣被廣東省佛山市順德區人民法院以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判處刑罰(11)。
三、刑事實務中“私家偵探”案件的辯護方向探析
現階段,“私家偵探”調查行為已被納入刑事法律評價范疇,雖然對其性質的認定趨向明確,但應看到與傳統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相比,“私家偵探”案件有其獨特性。
在傳統的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場合,不法分子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后,往往通過多次倒賣進行牟利。這些個人信息經倒賣落入社會不特定人員之手,極易被非法利用,滋生電信詐騙、網絡詐騙、敲詐勒索等違法犯罪活動。此類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的犯罪行為,不僅侵犯了公民的個人隱私,而且還嚴重威脅公民的人身、財產安全,社會危害性極大。
而“私家偵探”的調查業務均基于和委托人簽訂的委托調查協議開展,調查獲得的公民個人信息僅向委托人提供,而由于委托人與被調查的目標人員基本有某種特定關系(如夫妻、情侶關系),委托目的也相對明確(如確定伴侶是否忠誠等),因此委托人在獲得相關個人信息后,不會將這些信息進行二次擴散傳播,亦不會用于實施其他違法犯罪活動,使被調查人的人身、財產安全陷入高風險狀態或者造成實質危害。
不可否認,刑事實務中“私家偵探”案件裁判尺度趨向統一,客觀上對刑事律師的辯護工作帶來了困難,尤其在定罪層面,律師在此類案件的辯護空間確實越來越小。但在量刑層面,除了在具體個案中挖掘傳統的從輕減輕情節外,律師應結合“私家偵探”案件區分于傳統侵犯公民個人信息案件的上述特點,在社會危害性方面進行論證,為當事人爭取較輕量刑多做嘗試。